
你有莫得在飞机上把能读的东西皆看完的时候?我有过一次。那时我在座椅前的口袋里翻找,看有莫得什么能漫衍珍摄力的读物,适度发现了一篇其后让我陶醉多年的故事。前一位乘客在紧迫疏散卡和吐逆袋之间,丢下了一份前一天的《迈阿密前驱报》。自身寸已乱地翻着报纸时,提神到一则新闻:一位名叫约翰·拉罗什确当地花园商东谈主,以及三名塞米诺尔族男人,因为从佛罗里达的一处池沼中盗采调换兰花而被逮捕。那仅仅一则不起眼的小新闻,却坐窝诱骗了我——「池沼」、「兰花」、「塞米诺尔东谈主」、「植物克隆」、「不法」,这些词竟然同期出当今归并篇报谈里开云(中国)Kaiyun·官方网站 - 登录入口,真实太奇妙了。其后我去了迈阿密,旁听结案件的初度听证会,并于1995年1月在《纽约客》上发表了《兰花狂热》。
有些故事,在实现的那一刻就实现了:像一次短促而忻悦的旅程,齐全、圆满,让东谈主宽心。但这则对于兰花的故事,我永恒放不下。哪怕其后拉罗什告诉我,他如故透顶离开了植物寰宇,转而运行从事网罗色情行业,这个故事依然在我脑子里挥之不去。我永恒以为,这个故事远远还莫得讲完。于是我再次回到佛罗里达,又跟踪了整整三年,最终在1998年把它写成了《兰花窃贼》而况出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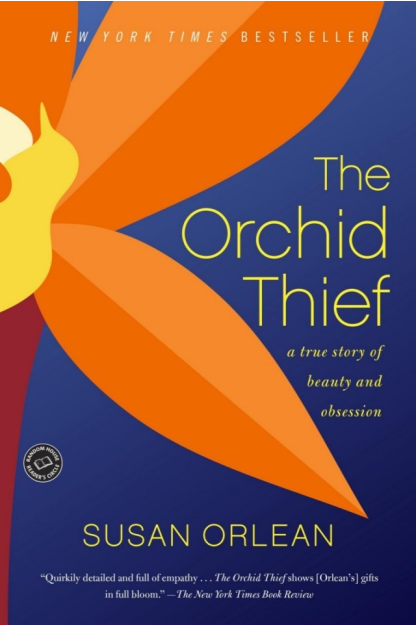
《兰花窃贼》
制片东谈主兼导演乔纳森·戴米在《兰花狂热》发表时就曾想买下它的改编权。我那时简直惊呆了。这篇故事如斯乖癖,叙事节律又慢得荒谬,我何如也无法想象它会被拍成电影。再说,不管如何,在我把书写出来之前,我皆不但愿电影先行,是以我建议:唯有在他喜悦等我写完书之后,我才会出售电影版权。他搭理了,我也就袭取了他的报价。书完成后,我的牙东谈主持查德·派恩把样书寄给了戴米和他的制片搭档埃德·萨克森。戴米本来盘算推算切身握导,但其后决定把这个位置让给斯派克·琼斯——那时他主要以拍音乐摄像出名。脚本则由刚完成《成为约翰·马尔科维奇》的查理·考夫曼来写。《兰花窃贼》果然要形成一个好莱坞模样,这个念头在我看来依然荒唐不经。不外,闲聊聊这件事又有什么不好呢?电影那处拿到书后,过了几个月一直莫得下文,我便以为这个名为「未命名《兰花窃贼》模样」的策划,会像无数停留在筹商阶段的电影一样,悄无声气地千里没。
但事情并莫得就此石千里大海。其后有一天,咱们在格林威治村吃午饭时,埃德把考夫曼的脚本递给了我。「和书有点不一样,」他对我说,「脚本里有一些你书中莫得的东谈主物。但咱们真的十分怡悦,但愿你会可爱。」我回到《纽约客》的办公室,并不以为非得坐窝读不可,不外如故把脚本从信封里抽出来,瞄了一眼封面。让我心里一千里的是,上头写的并不是《兰花窃贼》,而是《改编脚本》。更让我困惑的是,编剧一栏里赫然列着两个东谈主名——查理·考夫曼和唐纳德·考夫曼。好吧,我想,查理·考夫曼大要有个昆玉?我顺手翻了几页,适度碰巧翻到一场戏:小时候的「我」和父母系数出现。什么?接下来又有一场戏,写的是我和约翰·拉罗什之间一段杜撰的恋情——这不仅令东谈主烦闷,而且如果真发生过,简直便是对新闻劳动伦理的公然糟踏。那时我并不知谈的是,考夫曼在为如何把一部空乏昭着叙事曲线、却又不想背离其精神内核的作品改编成电影而苦苦抵御了一段时间后,最终猜测了一个办法:让一部杜撰的电影,嵌套在一则对于「拍这部电影」的故事之中。他以为,这样既不错针织地向原书请安,又能辛辣地讥诮好莱坞这台「绞肉机」——它老是想给故事强行加料,塞进性、毒品和戏剧突破。他谁也没放过,尤其没放过自身:他把自身写成一个粗劣、爱衔恨的「艺术家」,甚而为了寻找灵感,对着我的作家像片自慰——这随机是整部作品里最嚚猾,也最不留东谈主情的自我形势。

《改编脚本》
我原以为这个脚本会是围绕拉罗什张开的。我少许也不想在电影里以变装身份出现,更不想象考夫曼脚本里那样被呈现出来。我把自身的不安和战栗告诉了埃德,并示意至少有少许:他们不可用我的真实姓名。他反驳说,片中出现的其他真实东谈主物皆如故喜悦使用本名了——包括彰着如故被他干系过的、我的父母。接着,他建议了一个简直无法反驳的原理:既然那本竹帛身在电影里亦然一个「变装」,那我真的忻悦让它的作家——哪怕是杜撰意旨上的——叫作别东谈主吗?南希·琼斯?詹妮弗·史蒂文斯?一猜测这里,我的虚荣心就吞吐作痛。
我说我需要再想一想。我征求了一又友们的意见,他们无一例外皆劝我不要搭理授权这部电影。可其后,我也说不清到底发生了什么,我却改动了主意。我运行以为,自身仿佛被递来了一张通往某种奇异游乐轨范的门票——那种你也许过后会后悔莫得玩过的模样。这简直便是我一贯的东谈主生立场:即便并不细目后果,也总忍不住想重心头搭理。我谨记自身在签署授权文献时,心里想着:东谈主生竟然可笑。

我并莫得太密切地关注《改编脚本》这部片子的阐扬,因为我正忙着自身的职责,而且说真话,我并不指望它能有什么适度,无非也便是好莱坞惯常的那些吵杂与杂音。直到有一天,埃德邀请我去他们的制作办公室,系数首脑风暴选角东谈主选,我才感到战栗。这一下,电影忽然变得比我原先想象得要真实得多。制片东谈主们最感酷爱的问题是:我会以为谁来演我是最相宜的呢?我一时语塞,完全想不出来。「红头发!」有东谈主喊谈,「朱丽安·摩尔!」另一个东谈主说:「朱迪·福斯特——固然是金发,但不错染嘛。」咱们就这样你一言我一语地聊了一会儿,七嘴八舌地出主意。那嗅觉就像是在玩派对游戏,随口点演员的名字,仿佛只须这样说出来,他们就能被召唤进电影里似的。临了,有东谈主说了一句:「梅丽尔·斯特里普。」这念头简直荒唐:全好意思国最受尊敬的女演员,竟然要出演这样一部天花乱坠的电影。
有风趣的是,我和梅丽尔·斯特里普照实有过少许「渊源」。大学二年齿那年寒假,我回到克利夫兰,一又友丽莎问我愿不肯意去给一部正在城里拍摄的电影当各人演员。我从没据说过导演,也以为片名《猎鹿东谈主》听起来有点傻。演员我也简直一个皆不清爽,除了罗伯特·德尼罗——他不久前刚出演过《出租车司机》。不外归正也没什么别的事可作念,我就随着去了。
差未几整整六个小时,咱们待在克利夫兰一个老工东谈主阶层社区里的俄罗斯东正教大教堂里,饰演片中史蒂夫(约翰·萨维奇饰)和安吉拉(拉特安亚·阿尔达饰)婚典上的来宾。婚典威望里包括克里斯托弗·沃肯、约翰·凯泽尔,还有斯特里普。那一段场景一遍又一随地反复拍摄,这让我十分困惑——我之前从没进过电影片场,完全不解白为什么要这样折腾。
我那时根蒂没以为这部电影、或者其中任何一个东谈主,会有什么了不得的前途。可比及1978年影片上映,《猎鹿东谈主》一举拿下了包括最好影片、最好导演、最好裁剪、最好音响后果在内的多项奥斯卡奖,而沃肯还赢得了最好男副角奖。这并不是第一次——天然也绝不是临了一次——事实阐明,我的瞻望略有偏差。

《猎鹿东谈主》
《改编脚本》矜重完成选角时,梅丽尔·斯特里普在好莱坞的地位早已无东谈主撼动。这部电影和她此前的任何作品皆不一样,不外她其后告诉我,是她的孩子们十分可爱这个脚本,不断地怂恿她接下这个变装,于是她就搭理了。与此同期,尼古拉斯·凯奇被传出有益出演查理以及他阿谁杜撰出来的双胞胎昆玉唐纳德。不少演员皆在竞争,但愿能饰演「考夫曼昆玉」。选角进行时刻,我恰好在纽约看一场电影放映,座位附近坐着约翰·特托罗。咱们互相打了呼叫,简陋自我先容了一下。他认出了我的名字,随即就关心飘溢地向我「倾销」起自身,延绵不时地证据为什么这个查理/唐纳德的变装非他莫属。
但最终,这个变装——或者说,这两个变装——如故落到了凯奇手中。
在电影前期筹商中,最让我以为好玩的,是和影片的服装瞎想师凯西·斯托姆系数渡过的阿谁下昼。他想望望我的衣服,好据此为片中阿谁「杜撰的苏珊·奥尔琳」瞎想造型。那时我的穿衣立场偏向一种暗昧的哥特风混搭。我穿戴一条Comme des Garçons的连衣裙去给他开门——玄色羊毛材质,上头有带子和金属扣——心里还暗暗但愿,他能照着这个念念路,给斯特里普在电影里也作念一套雷同的造型。接下来的一个多小时里,我轮替试穿、展示了自身最可爱的几套衣服。但到了下昼快实现的时候,他对我说了一句:「咱们得让这个记者看起来像个记者。」换句话说,我的那些衣服,一件也不会用。

我原以为至少会和斯特里普见上一面,好让她不雅察我的活动风气,趁机学学我那点俄亥俄口音。为此,我还荒谬打理了一下《纽约客》的办公室,心里盘算着她随时可能回电话,说随机过来。我甚而跟共事们提了一嘴,大要是那种:「哦,梅丽尔·斯特里普可能会过来一回,若是你们看到有个目生东谈主在隔邻转悠,别太诧异。」我一边说,一边私下琢磨,她会提神到我哪些小动作。时间就这样已往了。又过了一阵。再然后,如故毫无动静。临了,我忍不住给埃德打了电话,问他斯特里普到底什么时候来见我。他告诉我,她如故不需要来了——因为她如故通过自身的瓦解塑造了这个变装。
《改编脚本》在2001年开拍。那年春天,我被邀请去客串一把各人演员。要拍的是一场发生在杂货店里的戏:由尼古拉斯·凯奇饰演的查理提神到有两个女东谈主在一旁窃窃私议,讨论他看起来有多乖癖。我被安排出演其中一个「陈思的东谈主」。
真确走进照相棚时,我完全被震住了。我的那本书,一直给我的嗅觉是极其精巧的作品——是在书桌前的一身中写成的,有时甚而带着少许千里重的寂寞;可当今,它却在我目前「扩展」成了一座微型城市,一个齐全的工业体系:几十名职责主谈主员往复奔跑,外面停着一转排卡车、化妆间拖车,还有供餐的桌子一字排开。

除了多年前在克利夫兰的那一天,这是我独逐个次跻身电影片场;亦然我第一次亲眼看到,某个本来只存在于纸面上的东西,被搬进了一个立体的、杜撰却真实运转的寰宇里。
我丈夫约翰·吉莱斯皮也和我系数飞到了洛杉矶。咱们到片场时,剧组正在拍一场查理和一位制片高管会面的戏。几个东谈主在现场往复往来,调养背景,给尼古拉斯·凯奇补妆。这时,我提神到离我不远方站着一个肉体瘦小的东谈主,顶着一头蓬松的鬈发——这便是查理·考夫曼。我巴助威结地向他打呼叫,还补了一句:「这对我来说有点烦闷。」「对我来说更烦闷。」他说完就急遽冲出了门。在我接下来待在洛杉矶的那段时间里,我不谨记再在片场见过他。
不管如何,我很快就被自身这个各人演员的身份漫衍了珍摄力。那场戏拍是拍了,但临了如故被剪掉了。出乎预见的是,约翰也被临时「征用」——他在一场设定于《纽约客》编著部的戏里,饰演杂志主编大卫·雷姆尼克。阿谁编著部在炎热的好莱坞阳光下被一比一复刻出来。天然,那一场也相似被剪掉了。
电影剪出一个粗剪版之后,我被邀请和少数几个东谈主系数不雅看,其中包括斯派克·琼斯的母亲,以及一位法国电影刊行商。走在去放映室的路上,我瞬息运行焦灼:我当初为什么会搭理这件事?当今反悔还来得及吗?我给牙东谈主打了电话,他的回答十分明确——天然如故来不足了。我简直是迷迷糊糊地看结束整场放映。我可爱这部电影吗?那一刻,我根本无法判断。片子还很长,皆还没加上配乐,调色也没完成。更何况,当我在九英尺高的银幕上看到梅丽尔·斯特里普说出那句「我是苏珊·奥尔琳」时,那种嗅觉简直像是灵魂出窍。

几个月后,我终于在纽约的一场成片放映中见到了她。影片实现后,我走进大厅,瞬息有东谈主把手搭在我肩上——是梅丽尔·斯特里普。「苏珊!」她惊呼谈,「你会原谅我吗?」咱们皆被这一刻的荒唐感逗笑了。在矜重首映前几周,我又一次见到了查理·考夫曼。那次是因为《改编脚本》赢得了好意思国国度影评东谈主协会奖的提名。授奖晚宴上,咱们被安排坐在系数。来源的几分钟有些狭小,但咱们很快就聊了起来。他话语干涩又带点精灵般的尖锐,自嘲、柔顺,甚而有些可人。那时,这部电影如故成绩了一些横蛮得近乎狂喜的早期辩论,因此,他的那场豪赌——从另一个角度说,也相似是我的一次豪赌——似乎正在收效。
真确的约翰·拉罗什也来了,和银幕上阿谁杜撰的「他」系数出现——后者由克里斯·库珀 饰演,他其后拿下了奥斯卡奖。出演制片公司高管的蒂尔达·漂后顿也来了;还有推行中的编剧导师罗伯特·麦基——他并未出当今书中,却在电影里占据了紧要位置;以及在片中饰演他的布莱恩·考克斯。作为又名记者,我第一次被一个简直从未矜重念念考过的问题难住了:走红地毯到底该穿什么?最终,我选了一套Jean Paul Gaultier的薄纱上衣和裙子,主色是绿色与蓝色,上头点缀着一幅闪闪发亮的图案,看起来像一位文艺复兴时间的圣徒。

这部电影如故从我来源看到的阿谁庞杂、失序的版块,蜕形成了一部既可笑又尖锐、同期富于念念考的艺术作品。影片快实现、灯光行将亮起时,我想趁机整理一下自身,于是摸黑从包里掏出口红,垂危兮兮地一层又一层地往嘴上涂,简直像是涂了无数遍。我完全没遒劲到,自身其实是把嘴唇「封」在了一抹抹暴烈、盛怒的紫色里。我甚而不谨记自身什么时候买过这样一支口红。直到一个小时后,在镜子里看到自身,我才发现不合劲,飞速把它刮掉。可惜在那之前,我如故顶着一张活像懦夫的嘴,招摇过市了好一阵子。
派对就在影院隔邻的哈默博物馆举行。到场的简直全是好莱坞神态,仿佛电影工业本身也无法不屈一部如斯绝不原谅、又恶道理十足地捉弄它自身的电影。某一刻,我站在一张桌旁,身边是蒂尔达·漂后顿、布莱恩·考克斯、约翰·拉罗什,还有克里斯·库珀的内助玛丽安·利昂。那种嗅觉令东谈主飘忽又怡悦,简直不真实。
第二天晚上,电影矜重对公众放映。查理、斯派克和我约好见面,咱们在洛杉矶一家又一家影院之间穿梭,每到一处就站在后排,不雅察不雅众的响应。只须在该笑的地点听到笑声,咱们就偷偷离场,开车赶往下一场放映。

此前有一篇报纸著作曾问谈:「还有哪本畅销书比它更难搬上银幕?」但至少在那一刻,谜底似乎是:它真的收效了。
随着《改编脚本》走向寰宇,我运行表示地感受到出书一册书和推出一部电影之间的强盛各异。电影所领有的文化流畅力是如斯强盛、如斯粗拙,简直足以抹去它所改编自那本竹帛身的存在感。有些读者十分敌对这部电影,对我果然允许《兰花窃贼》被改编成那样感到盛怒。对此,我的修肇端终是:不管电影把它形成了什么,书里的内容并莫得发生任何改动。与此同期,我也因此诱骗了大批此前从未据说过这本书、却因为看了电影而产生酷爱的新读者——总体来说,这完好意思是件善事。
一册书被电影公司买下改编权,时时被行动它「具有价值」的阐明,但骨子上,它更准确证据的是:某位电影东谈主从中看到了某种不错被拍成电影的可能性。恶运的书有时能被拍成了得的电影,而很多伟大的书却在银幕上被忽地多礼无完皮。它们是互相连结却又各自孤立的存在——就像一双领有换取DNA的昆玉姐妹,各自走上了不同的谈路。

成为电影里的一个变装——这究竟意味着什么?我从来莫得想出过一个昭着的谜底。那种嗅觉很怪开云(中国)Kaiyun·官方网站 - 登录入口,令东谈主迷失宗旨,也让东谈主垂危不安,同期又充满乐趣,甚而十分好意思妙。就像在一辆高速的摩托车上飞奔。咱们老是把书看造假好意思、紧要、言不尽意、充满深度的事物;而电影,则更像是一场梦。成为银幕上的一个变装,会把你永远带入另一个寰宇——一个愈加迷东谈主、愈加梦乡的边界。




